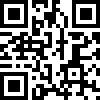蒋璟璟
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,一些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加。野猪属于保护动物,春拱种、夏毁苗、秋啃果,野猪增多,是生态环境向好、老百姓环保意识逐渐提高的体现,但野猪过多,影响农业生产甚至村民安全。广东、湖南、安徽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北等地山区庄稼都不同程度被野猪糟蹋。不少农民感叹,“辛苦种地一年,野猪一夜毁完”。(新华社)
生态环境持续改善,野生动物群落加速壮大。对于这一结果,不同的利益主体,想必有着迥异的体验。旁观者从抽象价值层面解读,自然赞之是巨大的进步。而作为亲历者,基于微观损益的角度考量,却也不免多有顾虑。近来年,与之相关的个案越来越多暴露出来。在很多时候、特定场景下,被保护的野生动物成了肆无忌惮“搞破坏”的一方,而农民反倒成了弱势的受害者。“打也不敢打,防也防不住”,这俨然是两难困境了。
由于法律起到的调节作用,野生动物和人类的角色反转,在某些地区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呈现。“辛苦种地一年,野猪一夜毁完”,受损农民们通常也只能是自认倒霉……这种极不对等的博弈格局,长此以往贻害无穷。
人与动物和谐相处,自然内含有人类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义务,但这同样不意味着,人类对野生动物无限度的让渡利益、自我牺牲。正所谓物极必反,一味纵容野猪等侵犯农民利益,很可能招致灾难性后果。比如说,激起非理智、群体性的“复仇”,农民们忍无可忍、退无可退,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不管不顾了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,过度失衡的、过于倾向于野生动物的政策机制,反倒会把野生动物推到人类的对立面、到头来反倒会害了野生动物。
保护野生动物,必须基于一种动态的平衡。诸如野猪、野猴等动物群落,在局部地区扩张过快、危害外溢,就必须采取果断手段及时应对,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乃至一发不可收拾。具体而言,若是一地野猪过多、繁殖过快,那么政府部门就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,第一时间组织专业狩猎队伍进行猎捕。以“保护动物”为由而拒不作为,任由农民庄稼被毁、损失惨重,这是极不负责的,也是对法律的误解与歪曲。
须知,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本身就有针对“种群调控”的专门安排,并就“限额猎捕”“特许猎捕”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。相关职能部门用足用好法律赋权,积极能动地履行职能,那么实现保护野生动物和人类权益的兼容,就是可以实现的。